《[大唐]武皇第一女官》[[大唐]武皇第一女官] - 已生變災(高昌國是有些晦氣在身上...)
太子乳母遂安夫人是一腔苦水實沒處倒,只好來陶枳這裏哭一哭。
待回去東宮,她便不會露出戚容,且得打疊精神,寬慰太子。
陶枳對姜沃嘆道:「方才遂安坐在這裏,哭濕了兩條帕子——還不敢用力擦,生怕擦腫了眼睛。明兒太子見了,哪怕不問緣故,心裏估計也猜得出。太子殿下,打小就是聰明敏慧的,很少有人能瞞過他去。」
又道:「那些朝臣們也是,便不肯說句軟乎話。」
被聖人欽點的幾位太子新師傅,確實都不是吃素的。張玄素於誌寧等人,哪怕在御前,也常有犯言直諫,並不知道留餘地的情況發生,何況面對個行為失控的太子了。估計恨不得一天梗著脖子諫八百回。
遂安夫人昨兒就恰巧聽見了孔穎達鏗鏘有力的勸諫,甚至還說出了『秦二世』三字,聽得不過四十來歲的遂安夫人差點心梗過去。
等孔穎達出門,見他依舊憤怒漲紅的臉,遂安夫人上前委婉勸道:「太子已經大了,都做了父親的人了,孔祭酒也當婉轉些勸諫,總不好當面如此。到底是折了顏面,只怕太子更不肯聽……」
孔穎達聞言,臉上堅定之色愈勝,比方才還鏗鏹頓挫道:「諫言皆出一心,對天地無愧,死而無憾!」說完大踏步走了,留下遂安夫人在原地直想哭。
若是為了利益,還能轉圜交還,可孔穎達張玄素等人,是真的心中信念就是如此:忠臣為國不惜身!太子錯了,我就要直言進諫,哪怕太子惱了砍了我的頭,只要太子聽了悔改了,大唐將來會有一位聖明君主,那死而無憾!
又不敢在東宮哭,只好來跟陶枳哭,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,要是長孫皇后還活着就好了!
姜沃走去給陶姑姑擰了條冷手帕敷眼睛,邊擰心裏邊在想這事。
她雖不似李治那樣真切感受到了太子的精分,但她從這些四方信息裏,也推斷得出太子是心理出了問題。
其實作為曾經的久病之人,姜沃還蠻理解太子的。
現代醫學已經注意到了心理疾病。尤其是她來的那個年代,比起一些疾病本身,那種被困在病床上的產生的心理負擔和負面情緒,越來越被重視起來。醫學上逐漸意識到,一個折磨人的病症哪怕是痊癒後,也會存在一個後疾病時期,要彌補心理創傷。
何況太子殿下從未痊癒,一直被困在令他覺得羞恥的病痛中。
太子是儲君,萬眾矚目的人卻必須跛足而行,心裏那份壓抑痛恥可想而知。
哪怕沒有跛足的壓抑,光來自君父的壓力,估計也夠大的。世上無新事,往前數一千年,往後數千年,熬不住太子位置壓力的皇子多得是。
許多人懷疑太子是被邪物侵體,其實差不多。
見陶姑姑這樣傷心,姜沃就撿著能說的安慰:「姑姑,您別難過了,您想,聖人點了這樣多賢臣去做太子師,也是響鼓用重鎚,積病用重葯。聖人若是真不想再管太子,便不會送這麽些舉足輕重的朝臣去東宮了。」
這些大臣甭管為了大唐還是為了自己,都會努力勸諫太子的——他們現在都擔著太子老師的名頭,太子若能一掃積弊轉為賢儲,他們就都是面上有光死而無憾的忠臣。
若是他們做了老師後,太子越發頑劣,以至於被廢,他們面上無光不說,將來旁人登基,也未必肯用他們這些『太子師』,前程亦跟着堪憂。
於公於私,他們起碼都會想着保太子。
因這幾年,魏王申請編書,欲為大唐編纂《地括誌》一套,身邊就圍攏了一群朝臣才子,如今人勢頗旺。
聖人想來也是注意到了,這回把許多重臣綁到太子車上去,既是懲罰也是回護。
可見現在,聖人還沒有下廢太子的決心,魏王還是備胎。
陶枳為太子為先皇后落淚半晌後,還不忘囑咐姜沃,如此局勢紛亂朝野動蕩,在太史局做事要一應小心。
說來不知多少人明裏暗裏,想從姜沃這裏打聽到(甚至是看她年輕想誆騙到)東宮星象是否有變。
但陶姑姑再掛心太子,不該問的,卻是從來不問。
她與媚娘都從未問過一句令姜沃為難的話。
然再慢的春日,終究是到了。春光從山腳下漸次染上來。
姜沃如今住的院中,有一株老桃花樹,此時滿樹花開。
媚娘正在樹下練習投壺,時不時有風吹過,桃花會落在她的發上、肩上,拂過她的面頰。
可媚娘生的實在是嬌麗,向來以『灼灼其華』著稱的桃花,竟叫媚娘的容顏比的素淡了下去。花瓣皆簌簌滑落,似不敢停留在她的面頰上。
姜沃進門時,看到的就是這樣的畫面。
美不勝收。
於是她也不進去,只在門口駐足,看媚娘投壺。
媚娘投的很專註。
按說投壺應當用木質沉重的拓木枝,哪怕有些微風,也不會影響準頭。但拓木貴重,媚娘弄不到那樣正式的投壺拓木,卻也無所謂,直接撿了尋常樹枝來投壺。
姜沃見媚娘把幾支樹枝精準無誤都投送到壺裏去。
這才在門邊海豹似鼓掌。
媚娘聽到聲音側頭望去,見她回來就笑了,眉目間是這些時日少見的歡喜:「小九兒的命已然保住了。今早我去看了一眼,精神都活潑起來,肉也照吃不誤。瞧著比從前胃口還好。」
雖說不能奔走敏捷如旁的猞猁,但小命總算保住了。
「聽獸苑的人說,晉王還吩咐過,等聖駕離開九成宮,就把小九兒也帶走。」媚娘越發放心了,不然他們一走,聖駕很可能幾年不來,說不得小猞猁就沒了。晉王肯帶走最好,只要他偶爾去看一眼,宮中獸苑就不會苛待這隻瘸腿小猞猁。
姜沃踩着地上斜斜的樹影走過去:「那太好了。」
她從壺中取回所有樹枝,坐到媚娘旁邊去,也試著投了一個,只見樹枝擦著壺口過去了。
而媚娘起手再投,又是穩穩中壺。
姜沃好奇起來:「姐姐為什麽忽然苦練投壺?」
媚娘原先投壺可沒有這樣好——投壺在宮廷中是很流行的小遊戲,年節下宮人會有幾天被允許組織投壺比賽,人人都可以下注,算是官方允許的一種□□行為。
前兩年過年,媚娘和姜沃也參加了宮正司內部的投壺賽,水平只能算是『重在參與』級別,根本贏不到好的彩頭,只能拿一塊麥芽糖。
怎麽現在媚娘就這麽技藝精準起來。
媚娘道:「我這幾日每天都在苦練。」指了指旁邊的書:「還專門學了《投壺經》。」
「北漪園那幾個才人們之間傳著,十日後,聖人要帶著幾位皇子並王爺們去圍獵,等到歸來之際,還要在後宮行投壺賽——今年不賽馬球了。」
媚娘並不知道自己參加投壺賽會不會像之前一樣,哪怕表現出眾,依舊不被聖人喜歡。甚至不知道,韋貴妃組織的妃嬪投壺賽,她有沒有資格去參加。
但她還是苦練了,完美闡釋了『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』,而她永遠是提前準備的人。
姜沃心道:也就是得寵這件事是玄學,基本靠命。要是是考公這種有題目有標準的擇選,以武姐姐的聰明好學和堅韌毅力,怎麽著也能得個寵冠後宮的分數。
唉,偏生得寵不是考試,根本無從預料。
比如韋貴妃,哪怕長孫皇后在時,她也是最得皇帝喜愛的嬪妃之一。但其實韋貴妃入宮的時候,所有人都不看好——如今宮中已經很少有人提起這樁舊事:韋貴妃是二嫁之身,甚至跟前夫還有一個女兒。
其前夫在隋朝因罪被殺,而彼時還是秦王的皇帝,出於一些政治目的,需要穩定洛陽士族的心,才納了當地大族韋氏之女。
這樣的開局,實在是比媚娘還差些。但韋貴妃就是得皇帝喜歡,皇帝剛登基就封了妃嬪之首的貴妃,膝下還有一兒一女,在後宮很是得意。
可見得寵之事,實在沒處說理去。
姜沃投了幾次都是擦瓶而過,就拿起矮凳上放著的書:「姐姐是看了什麽秘籍嗎?投壺還有專門的書?」
媚娘道:「是,寫的還很不錯呢。文采斐然,引經據典,將自古來投壺的禮儀也考據的明白。」
掖庭裏投壺,是純看準頭。但嬪妃們投壺就繁瑣鄭重的多了,處處要遵循古禮,很講究儀式感。媚娘就早早學習起來,免得到時候舉止失當,讓人笑話。
姜沃就翻過去看扉頁:「這是誰寫的?」
媚娘的聲音與姜沃的目光同時落在一個人名上:「上官儀。」[1]
姜沃:……
到目前為止,媚娘所見的文臣墨客作品不多,唯二讓她誇過的偏偏是駱賓王和上官儀。
緣,妙不可言。
*
媚娘到底沒有參加成投壺賽。
不過,不只是她沒有參加,而是投壺賽根本沒有舉辦,連聖人的圍獵也取消了。
朝上發生了一件大事,皇帝根本無心圍獵。
「聖人真的把侯將軍下獄了?!」
陽春三月,最好的春光,九成宮內氛圍卻有些壓抑。
聖人大怒,誰能歡喜?
劉司正、於寧和媚娘三人正坐在一張桌前,一並抄錄近來受罰的宮人名籍與懲處措施。
媚娘是被拉來幫忙的。
劉司正早就練就了邊說話邊抄寫,依舊字跡端正的本事:「這再沒有假的,侯將軍已然下獄了!」
於寧沒有這份一心二用的本事,她停下了筆,才詫異問道:「可是侯將軍剛攻破高昌,大勝歸朝啊。」
媚娘低頭抄著,耳朵卻沒有漏下一句話。
她們所說的侯將軍,正是曾官拜兵部尚書、光祿大夫,四年前加封陳國公,去歲剛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,大敗高昌的大將軍侯君集!
-
連載中116 章

震驚!青梅竹馬未婚夫居然有白月光免費閱讀
柯然聽到這話臉上的表情彷彿吃了一把蒼蠅……聞溪說道:「我們走吧。柯然立刻點點頭,拉着笑笑跟上,陳緣看着不遠處的聞溪頭也不回的上了車心裏越發不是滋味。車上,笑笑的嘴巴依舊沒有合攏,還沉浸在剛才的畫面給她的震撼里,柯然看到笑笑的表...
-
連載中116 章

蘇萌萌林文清最新小說
幾分鐘過去。現場,已經沒有一個黑衣人存活下來。小林將手中的手槍甩出。再次大吼一聲,好似在宣洩着心頭的不滿。「小林叔叔,你好厲害啊。突然,身後傳來一聲稚嫩的女聲。小林正準備回話。突然,感覺到一陣不對勁。話到嘴邊,被生生咽下。小林轉過身來,蘇萌萌不知道什麼時候,已經來到了他的身邊。此...
-
連載中116 章

萬倍返現,大明星成了我的女友
上岸先斬意中人,我就被斬的倒霉蛋。天無絕人之路,天降萬倍返還系統,偶像美女大明星,公司御姐女總裁,鶯鶯燕燕的高分的美女,都成為我的舔狗。從此左擁右抱,腳踩財閥,掌摑二代,踏上巔峰!人生如此多嬌,我的腰!
-
連載中116 章

鳳青幽墨祁雋
醫毒雙絕的王牌特工鳳青幽穿到大周國一草包身上,一穿過去就被賜婚給毀容殘疾的九王爺。 九王爺身中奇毒,被御醫斷言活不過三個月,鳳青幽放出豪言三個月之內必定能治好九王爺。 全京城的人都盼着看她的笑話。
-
連載中116 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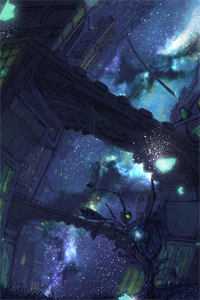
暴君家的小奶團她恃寵而驕
書名叫做《暴君家的小奶團她恃寵而驕》的古代言情小說是難得一見的優質佳作,瑤瑤嘉和帝兩位主人公之間的互動非常有愛,作者「琴秋塵音」創作的精彩劇情值得一看,簡述:第4章這個少年本是北燕皇子,但因為宮變流落到大楚,陰差陽錯成了顧駙馬的庶子。在未來,他會殺回北燕,奪回自己的王位!那些欺....……...
-
連載中116 章

太子,收手吧,咱們已經舉世無敵了!
一代殺手之王穿越到了一個懦弱的廢太子身上。開局就面臨,廢除太子身份,驅逐出境,永世不得回國的境地!大皇兄綠我,貴妃欲要致我於死地!丞相虎視眈眈欲要篡權奪位。皇叔勾搭內宮,圖謀造反!他媽的!這還能忍?廢太子默默仗劍起身。從今天起,這個大秦,就由我來鎮守!


 上一章
上一章 下一章
下一章 目錄
目錄